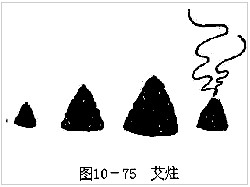您的位置:首页 > 中医常识 > 中医诊断 > 诊断基础 > 宋元以降医书、医案、方书中脉法的位置与应用
宋元以降医书、医案、方书中脉法的位置与应用
宋以来医学专著与专科著作日多,但是此时方书、脉书分成两个系列的形式已经定型,其中尤其是脉书以脉为主列出病证的形式的影响所及,在医书著作里亦多是论列证候治治疗而不及脉,亦以两个系列的形式出现。我们看朱元以下的综合性临床医学著作中,往往都单有脉学的一部分专篇专题等,某些专科书亦有这种情况,如元·齐德之的《外科精义》就有专篇的脉诊著作,它与一般脉书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更重视有关外科问题而已。明后叶王肯堂著《证治准绳》徵引极广,自河闻、洁古、东垣以下,所论病证治法,极少联系脉象,故尔《证治准绳》在每病之后,加“诊”一项,其中以脉诊为主,亦是以病证与脉分两个系列的一种形式,这与平脉辨证之法显然是不同的。
当然例外的情况亦是有的,如李东垣根据当时出现的一种新型疾病,他命名为劳倦内伤,在大量的实践和取得卓著疗效的基础上制定补中益气汤,著《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他的这段经历、成就和著作,有些像是仲景之于伤寒。就在他所著的《内外伤辨惑论》中有“瓣脉”一篇,确是结合证候脉像进行论辩分析,与一般单纯以脉列病性质的脉书脉论有所不同。
“辨脉”说:“古人以脉.上辨内外于人迎、气口,人迎脉大于气口为外伤,气口脉大于人迎为内伤。此辨周是,但其说有未尽耳。外感风寒皆有余之证,是从前客部来也,其病必见于左手,右手主表,乃行阳二十五度。内伤饮食及饮食不节,劳役不节皆不足之病也,必见于右手。右手之里,乃行阴二十五度。故外感寒邪则独左寸人迎脉浮紧,按之洪大,紧者急甚于弦,是足太阳寒水之脉,按之洪大而有力,中见手少阴心火之脉,丁与壬台,内显洪大,乃伤寒脉也。若外感风邪则人迎脉缓而大于气口一倍,或两部、三倍。内伤饮食鼬右寸气口脉大于人迎一倍,伤之重者,过在少阴则两倍,太阴则三倍,此内伤饮食之脉。若饮食不节,劳役过甚,则心脉变见于气口,是心火刑肺,其肝木挟心火之势,亦未薄肺。《经》云:‘侮所不胜,寡于畏’者也。故气口脉急大而涩数,时—代而涩也。涩者肺之本脉,代者元气不相挟,脾胃不及之脉,洪大而数者,心脉刑肺也,急者肝术挟心火而反克肺金也。若不甚劳役,惟右关脾脉大而数,谓独大对五脉,数中显缓时一代也,如饮食不节,寒温失所,则先右关胃脉损弱,甚则隐而不见,惟内显脾脉之大数微缓时一代也。宿食不情则独右关脉沉而滑,《经》云:‘脉滑者有宿食也。’以此辨之,岂不明白易见乎?但恐山野间卒无医者,何以诊候,故复说病证以辨之。”比较系统余面的述论分析了内外伤脉象证侯的各种变化和关系、性质等。这是他在对内伤外感深刻研究实践体会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而在《脾胃论》的各篇各证却无360足球直播app:脉象的或脉证结合的论述分析,显然在李东垣的认识上仍然是以脉和病证做为两个系列的,若非他对内伤外感这个问题有非常深人的研究和认识,恐怕不会去写这样的一篇文字的,亦写不出这样的一篇文字。其他则认为脉的问题自有脉学书在,在论病时无须赘述。这在对脉证对比分析认识做出了贡献的李东垣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另外在“辨脉”的最后李氏说:“如恐山野间卒无医者,何以诊候,故复说病证以辨之。”这说明他意识到在这里谈一大段脉法是有些特殊,不符合一般作为两个分列的要求,所以要作一下解释说明。其实李氏此说上继《内经》仲景,亦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基本做到了病、脉、证的分析对比综合判断,从而达到平脉辨证的要求是一个系列性质的,不是两个系列性质的。就是不在山野间而是”通都大邑”求医不难,那些医者能做到李氏韵要求么?可见东垣虽然上继《内经》、仲景,做出贡献,但对贡献的意义,却认识不足,于此亦可见两个系列影响之深。在各家论病论证时偶尔亦点出脉法但非常之少,只是只言片语而已。其思想认识亦与李氏类似,认为只有脉书才讲脉,或脉应单另讲,这种形式上的限制影响辨证论治的发展是很大的。
在医案中脉象使用的记载要较多,但已不是或不完全是仲景以前(以《内经》为主)的法脉了。原因是后世医家虽知尊崇仲景,但很多人有仲景只精于伤寒的偏见,同时叉受历代方书、本草书简单形式的影响,加以洁古的古方今病之说,河间的古方难用之论,所以多避难就易,同乎流俗,很少人能真正上继忭景平脉辨证之法。另外一个因索是脉诊到此时作为一个独特的系列早巳完成,要用就得按照脉书的以脉为主论列病证的方法。具体到医案中就是见到什么脉就依照脉书的说法去与病证对号就是了,失去了仲景的脉证参合分析,不为常法所拘的有常有变韵辨证论治的形式和方法。后人虽然亦说脉证合参等等,但只不过是配合起来使诊断辨证的依据更为全面一些而已,很少有像仲景著作中那样的平脉辨证方法。宋元以下的方书仍然是沿袭传统的型式,虽列病证亦都是“说明书”性质的,不具有脉法及平脉辨证性质的内容。
根据以上脉法的演变过程及从方书、医书、医案等内容上分析,长时期以来作为两个系列的情况是很明虽的。前人论脉虽然亦提到过若干具有辨证意义的说法,如浮脉未必主表,沉脉未必主里,浮脉“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及结代脉有可能体质如此未必主病等等,但仍是在脉法的立场和角度上说的。后来徐大椿作《洄溪脉学》前以脉证两两分析论述,多取材于《内经》、仲景,亦有个人心得体会,是符合脉诊方法在辨证论治中的性质和地位的。但这种类型的著作不多,为时亦已过晚(清中叶)且篇幅不大,内容亦简,没有受到更大的重视和起到甚么大影响。
总之,自《脉经》以后,脉法或为独自的系列,在医书、方书等医学书籍中,没有什么地位,以致不但脉学的发展受到限制,对《内经》、仲最的在脉证上的具有辨证意义的理论和临床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亦受到限制,这个问题应当是今后脉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